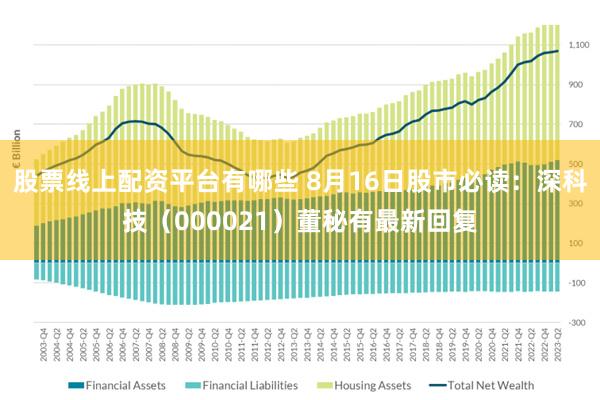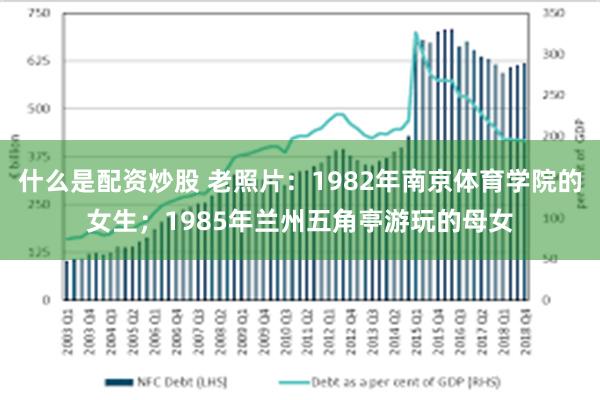上海解放前夕,我五岁,住在老城厢的长生街。路是弹硌路,路面铺花岗石块线上配资门户网,一场暴雨后,石块洗得干干净净,铮亮铮亮的。长生街也不太平,昨天,隔壁孤老太家就被抢了,警察局装模作样地来查查,后来就不了了之。老太婆却逃掉了,哪能逃脱的?啥人也不知道,只有我和隔壁小山东晓得,她家里头有个地道,地道有扇小门,出门就到了民国路,老太婆从地道逃跑了。
我爸妈是送报纸的,每天很晚回家。傍晚下雨了,他们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,我忙凑近爹爹耳朵说:“他,朱,猪头三回来了!”我们楼上住三家,“猪头三”是毛头姆妈的老公,警察局的一个头头,凶得不得了,平常很少来,今天我上楼去玩,看到他们家门背后挂着根很粗的皮带,是警察的皮带……
“怪不得啊!”听我讲完,爹爹急促地叫我马上去楼上找范家伯伯下来。
“不要多管闲事!”姆妈一把拉我到身后。
“侬懂啥事体?儿子快去!”

我们顶楼上是范家。范先生在一家商行做会计,和范师母住。大女儿出嫁了,大儿子长林在读大学,很少回来。我上去一叫,范先生就轻轻下楼来。他还是那老实巴交的模样,头上罗松帽皱皱巴巴的,近视眼镜一条腿断了用绒线绳挂着。听爹爹问:“长林今朝回来伐?”他吃了一惊,说不出话。“你们家的事,我都晓得。我送报的,闻不出油墨味道啊?”爹爹说着,指指楼上毛头家,“他回来了,要来捉人的。”“那,哪能办?”范先生不知所措。
外面的大门轻轻响了,随即进来个人。是长林!他穿着件旧大衣,戴顶呢帽子,浑身上下都已湿透。等他上楼,爹爹 就一步蹿出把他拉进屋里。“出事了?”看到范先生,长林就似乎明白了。听说长林明天一早就要走,而现在约了朋友来,爹爹就明白了:“能叫你朋友不进门吗?”他好像很老练的样子,“有什么暗号?”他又忙着补充一句,“你们的事情我都晓得,在为我们穷人做事!”长林激动地拉住爹爹的手说:“谢谢您汪叔叔。”说着脱下大衣和帽子,“您穿上我的衣服,到门口喊,快回家吃晚饭了,就行了。抓,就抓我一个,没关系!”“不,侬也要逃掉!”爹爹立刻回头吩咐我,“你陪长林到自己家,从天窗出去,翻屋顶逃。”说着拿起自己的雨衣给长林,“穿上我雨衣,把侬大衣给我!”接着,又拿来几只馒头塞给长林,“路上吃。自己小心!儿子,快点上楼!”随后就冲出了大门……
我陪长林从屋顶天窗进入那家被抢的孤老太家,从她家地道出后门到民国路。那里的有轨电车环城开,一会儿就能到十六铺码头。我给长林一一讲清楚,他就笑着摸我脑袋:“年纪小小,还很会动脑筋的。好好读书,将来派大用场呢!”
第二步:蒸熟的南瓜块放在大碗中,倒掉多余的水分,再将南瓜块压成南瓜泥,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白糖;
眼睛一眨,半年多过去。新的一年到了。姆妈还常叹气:“现在一麻袋钞票还买不到一麻袋米。”爹爹却总笑呵呵说:“快了,快了,好日脚会来的。”黄梅天,雨水更加滴滴答答不停。这天早晨推开大门,我一看,呆住了:长生街沿街各户门口,地上都躺着当兵的人,弹硌路还是湿的呀,许多兵士的衣裤都湿得捏出水来了,可他们照样抱着枪互相背靠背睡着了。太累了,实在太累了。曙光从屋檐透过,照在那草绿色军帽上,红红的五角星闪着红光,蛮好看的。爹爹到路边,看见一个娃娃模样的小兵,拉住他,叫他无论如何 进屋休息,他却“啪”地行个军礼:“谢谢。这是部队纪律!”
这几天,《申报》停了,可是有人通知爹爹去报社拿《上海人民(号外)》送。爹爹送了200多份,还带回来一张,印着“大上海解放了,解放军约法八章”,还有“惩处战争罪犯命令”,日期是五月二十五日……爹爹仰着头,眯住眼睛慢慢地说:“他回来了,在军管会当官了,是长林。”
长林哥哥后来到过我家,边喝着姆妈烧的“面疙瘩汤”,边告诉我们,那个“猪头三”已经被抓,老太婆被抢一案是其所为,监守自盗。范先生家搬走后,我们也去过。范长林后来去了北京工作。我结婚后知道,妻子唐福妹的大哥唐和定解放前也是我地下党员,上海解放初就担任杨树浦自来水厂厂长。两亲家聚会时,爹爹讲起当年救助范长林的事,我详细追问,才了解许多细节,也想起了那些久远的记忆片段。
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送报送信的邮电工人,一生正直线上配资门户网,教我做人的道理,谨以此文纪念他们,并纪念上海解放七十五周年。(汪正煜)